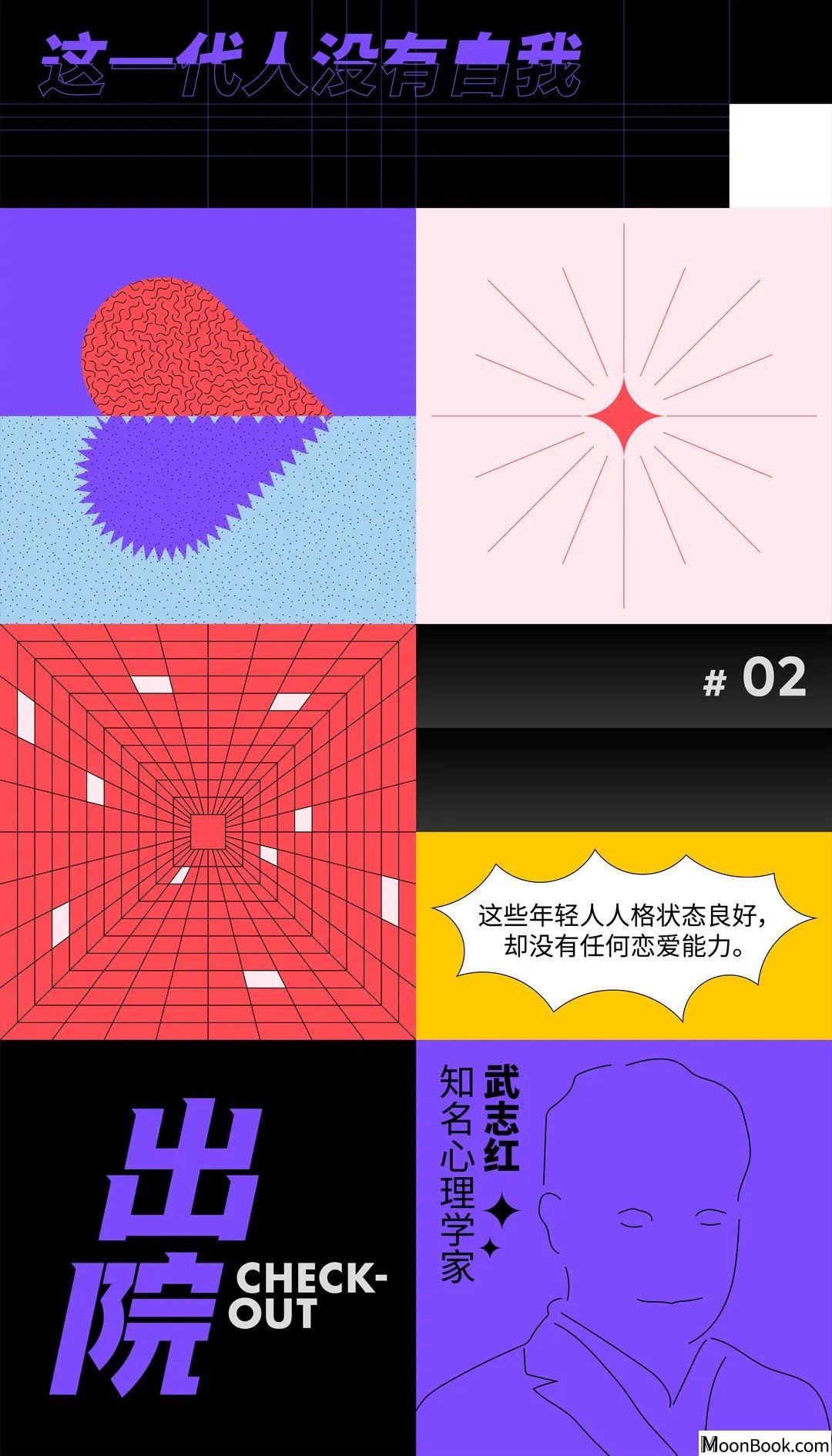各种TED演讲、每日冥想练习、年度世界幸福报告、关于如何保持积极心态的建议……身边的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快乐在人们的生活中有多重要。虽然这个概念至少从亚里士多德在探究Eudaimonia(希腊语,一般被翻译为人类的幸福或者福祉)的意义时就被提出了,但是对幸福本质的研究——也就是积极心理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才刚刚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萌芽。
积极心理学非常复杂,它涉及到东方宗教、神经科学、进化生物学、行为经济学、国家间的比较和公共政策间的关联。不过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心理学家的关注点从精神疾病转移到了精神健康,从焦虑抑郁转移到了主观幸福。

我们感到更快乐了吗?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发表于1952年的自助书《积极的力量》虽然遭到了精神健康专家的批评,但直到现在也很有影响力。—Wikimedia Commons
讽刺的是,积极心理学诞生于痛苦与战争——与它现在强调的积极人类功能以及恢复力的科学研究不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刚刚起步时,它更侧重于自我意识与制度重要性。
人能从极其高压的经历中受益,这曾是积极心理学最有影响的发现之一。精神病学家以及集中营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的经历比任何人都能证明并解释创伤后的个人成长。从1942年的九月起,弗兰克在纳粹集中营被困了足足两年半之久。
被释放不久后,他便开始攥写《无论如何也要对生活说好》(Saying Yes to Life in Spite of Everything),并于1946年以德语出版。1959年,该书于美国出版,并最终改名为《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在战后回到维也纳后,弗兰克对这段如此可怕经历的回应是:最可怕的环境也可以是幸福的温床。
如果说弗兰克是在极端苛刻的条件下经历了痛苦,那么处在特权阶层的约翰·鲍比(John Bowlby)则面对了相比弗兰克而言不那么戏剧化的苦难。童年时代的鲍比鲜少见到他的父母,这让他的一生都在关注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在他1951年的报告《母爱行为与精神健康》(Maternal Care and Mental Health)中,他基于对二战后数百万失去家庭的儿童的研究得出了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依恋理论随后被其他科学家延伸并补充,让它更普遍地强调了社会关系对人类幸福的重要性。

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日前夕,二战老兵访问士兵公墓—法新社
那些二战老兵极大的创伤经历同时也塑造了艾伦·贝克(Aaron Beck)的理论。他写成了一本关于抑郁极有影响力的书,同时也创立了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一些他最初发表的论文里面记录了意外杀死了同伴的老兵们的反应。
贝克凭此创立了测量以及治疗因类似创伤经历导致的精神疾病的方法。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是教导患者提出替代的解释、建立合乎实际的目标、学会客观面对现实以及练习“中立化‘自动思维(automatic thoughts)’”。这样,如果一个人不幸福(虽然贝克不怎么用幸福这个词),至少ta会以一个不压抑且合乎实际的方式面对这个世界。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他主张的积极、人本心理学源于个人和社会的逆境。作为一个悲惨不幸的母亲之子,他小时候就遭遇了反犹太主义;此后,作为一位年轻的心理学专业人士,他认识了许多因纳粹而流亡的心理学家。这些经历促使了马斯洛研究出了一个全面且积极的关于动机的理论。
这个理论提倡了人类个体如何渴望自我实现。他关注那些健康且有成就的人,将注意力放在常态而非异常上。马斯洛的视角在其1954年的作品《动机与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得到了最为有影响力的表达。他在书中完整地阐述了他对自我实现的定义。他的解释基于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作为最强烈的体验立于需求层次的顶端。
如果说弗兰克、鲍比和马斯洛解释了关于幸福的一方面,那么神经科学家们就解释了另一方面。詹姆斯·奥尔兹(James Olds)发表于1956年的《大脑的愉悦中枢》(Pleasure Centers in the Brain)就成为了其中的一项重要发现。
在《科学美国人》里,奥尔兹写道,刺激大鼠大脑可以让它们得到快感,而这与“刺激大脑就等于惩罚”的假设相悖。他表示,希望后续的研究可以定位这些受到电极或药物刺激就会满足某些基本需求(比如饥饿感与性欲)的神经细胞。

Supriya Bhonsle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科学家们发现不仅电刺激(electrical stimulation)可以使人快乐,药丸也可以。这十年里,有些被称作“快乐药丸”的处方药即便不能带来快乐,也至少能降低焦虑感。或许正如1958年一位观察者在一本加拿大医学杂志里所写的一样,“获得幸福的灵丹妙药已经被找到了”。
眠尔通(Miltown)是第一批在缓解社交、医疗以及心理痛苦上较为管用的镇定剂。它的诞生也展示了研究科学家弗兰克·博格尔(Frank Berger)如何从一个逃出纳粹集中营后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变成政府实验室的细菌学家。1950年,他和一位同事合成了能将暴躁的猴子变得温顺亲人且警觉的眠尔通(Miltown)。经历了漫长的启动之后,它成为了第一个轰动全美的精神药物。
另一个科学与幸福间非常不同的联系,源于第一个关于幸福感的长期社会学研究——它虽然诞生于对于心理疾病的担忧,却很快变成了对于幸福感的探索。
《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心理健康:一项全国性的调查》(Americans View Their Mental Health: A Nationwide Interview Survey)的作者们记录了一些采访。一些美国人在采访中被询问道他们“是否幸福、是否忧虑以及觉得自己究竟是悲观还是乐观”。研究者们旨在弄清人们对于生活的感受。如果他们遇到了问题,是否会、会向谁寻求帮助——这项研究同时也更关注专业帮助而非患者自助。最终,他们总结道:大约9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非常幸福,或者至少还挺幸福的。
五年之后,一项研究又将注意力从心理健康转向了主观幸福感。在《幸福感报告》(Reports on Happiness)中,社会心理学家诺曼·M·布拉德伯恩(Norman M. Bradburn)以及社会学家大卫·卡普罗维茨(David Caplovitz)首次关注起了被他们称作“正常人”的幸福感,并呼吁研究者们多多关注“积极的满足感”,而不是心理问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反主流文化留下了对幸福的新研究、对毒品的新实验、对东方宗教的兴趣、对冥想的实践、对人本心理学的信奉以及一种认为尤其强烈的经历比商品更令人快乐的观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这些都是艾伦·瓦特(Alan Watts)生活与写作中常常出现的元素。作为美国浪漫史的代表人物,他因为觉得现实世界并不能给予他生活之道与创作灵感,将注意力转向亚洲宗教。
*译者注:西方在二十世纪晚期一种反对遵从资本主义理性文化道德法规及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浪潮。
然而,瓦特对于禅宗佛教以及道教的信奉,与他远非平静的生活形成了无法解决的强烈矛盾。为了追随超验主义,他不停酗酒,直至自己达到另一种意识状态;尽管他崇尚简朴,但他不得不养活一个妻子、许多前妻以及七个孩子。他在1961年写道,要想获得幸福,就必须重新连接现代生活所割裂的东西——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个人”与“未知的自我、无意识的内在宇宙”之间的关系。
在他非常受欢迎的《禅之道》(The Way of Zen)中,他把冥想描述为“一种安静的、对此时此地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加评论的意识”。虽然一开始对使用毒品持怀疑态度,但到了1962年,他便将LSD誉为“快乐宇宙论”的入口。
尽管许多积极心理学的基石都构建于苦难,其中还是有一例外: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发表于1952年最有影响力的著作《积极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成为了最为广泛阅读的积极心理学先驱(尽管积极心理学的实践者们都尽量与这本书保持距离)。
皮尔在书中传递出一种非常令人安心的信息,即疗愈性的、新教徒式的心灵操控必能带来安宁、快乐与福祉。尽管他也会举出一对一帮助他人的例子,他的愿景仍是高度个人主义的。
1998年,在皮尔成为美国心理学协会会长的任命会里,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马丁·P·塞利格曼(Martin P. Seligman)正式宣布积极心理学成为一门学科,尽管此时这一领研究领域的许多组成部分已经独立存在。积极心理学家会借鉴前人的经验,而且往往是以这些前辈无法预料、也不会赞同的方式。尽管如此,积极心理学仍是一个强大的新领域。它以科学为基础,并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
原文:https://www.zocalopublicsquare.org/2018/04/27/modern-psychologists-focus-happiness-roots-worst-human-traumas/ideas/essay/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 作者:Daniel Horowitz,翻译:NZ